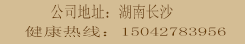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政治 > 保罗巴奇加卢皮黄卡人下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政治 > 保罗巴奇加卢皮黄卡人下

![]()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政治 > 保罗巴奇加卢皮黄卡人下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政治 > 保罗巴奇加卢皮黄卡人下
陈试图抑制饥饿感,强迫自己转身离开,但他做不到。他知道有些特别爱面子的人,宁可饿死也不会吃马平的残羹冷炙,但他不是这种人。或许在很久很久之前,他也是。但他的新生活带给他的羞辱让他明白了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些甜蜜的幻想现在已经离他远去。他坐了下来。姓马的满脸笑容,将剩下一半的饭菜推到陈面前。
陈认为自己一定是前生造了孽,才会在今生遭到这样的羞辱。但尽管如此,他仍然需要极力克制直接埋头于油腻的盘子之中、用手指进食的冲动。终于,街边小吃摊的摊主送来了一双吃粉的筷子,还有吃其他菜品的叉子和勺子。米粉和小块猪肉顺着喉咙滑了下去。他试着咀嚼,但只要舌尖一碰到食物,他马上就会吞咽下去。更多的食物倾泻而下。他端起一只盘子,将姓马的吃剩的东西全部倒入口中。鱼肉、细长的胡荽和浓稠的热油滚滚而入,就像上天的恩惠。
“好,好。”姓马的朝着夜宵摊主挥了挥手,要来一个酒杯,倒上酒递给陈。
姓马的刚开始倒酒,酒香就在他身周缭绕。闻到这个气味,陈不禁胸口发紧。在刚才的匆忙中,有一些油留在了他的下巴上。他用手臂擦了擦嘴,眼睛盯着倒入玻璃杯中的琥珀色液体。
陈喝过法国白兰地XO,是他自己的快速帆船带回来的。由于船运的成本,那种酒的价格昂贵得不可思议。那是收缩时代到来之前,洋鬼子们带来的口味,是来自过去的幽灵。随着新扩张时代的来到,陈自己也意识到世界再次越缩越小。就在那时,这个幽灵又被发掘出来,受到了欢迎。随着新的船壳设计方案和更先进的聚合材料投入使用,他的快速帆船舰队可以环游世界,带回许多传说中才有的东西。而马来买家也很愿意为此买单,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那是多么丰厚的利润啊!他强压下这些思绪,在姓马的示意之下碰了一下杯,然后端起酒杯大口喝下。那是过去的事情了,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他们痛饮了一番。烈酒与刚才吃下去的小辣椒、鱼肉、猪肉和炒面的热油汤混在一起,让陈的肚子里暖洋洋的。
“你没有得到那份工作,我真的很遗憾。”
陈皱起眉头,“别幸灾乐祸了,命运是公平的,我已经学到了这一点。”
姓马的挥了挥手,“我从不幸灾乐祸。但我们人太多了,这是没办法的事。你的水平比那份工作的要求高一万倍,任何工作对你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他啜了一口威士忌,透过酒杯的边缘看着陈,“你还记得吗?那时候你说我是一只懒惰的蟑螂。”
陈福生耸耸肩。他的眼光无法离开威士忌酒瓶。“我还骂过你更难听的呢。”他等着看马平会不会再为他倒满酒杯。他好奇这家伙到底有多富有,这慷慨的赠予能持续多久。但与此同时,他也憎恨着这样的自己:在一个曾经被他开除、如今地位却远比他高的年轻人面前扮乞丐……而这个年轻人现在又很给面子地为陈斟满了酒杯,酒液甚至从杯口溢了出来,在蜡烛晃动的光线之下犹如一道琥珀色的瀑布。
姓马的抬起瓶口,注视着溢出来的酒液。“真的,这世界简直天翻地覆了。年轻人爬到了老人家的头顶上。马来人让我们华人吃了苦头。洋鬼子们又回到了我们的海滩上,就像苦水病暴发后被冲上海岸的死鱼。”姓马的微笑着,“你得竖起耳朵,了解每一个招聘信息。不能像待在人行道上的那些老家伙那样,专门等着干苦力活儿。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吧。我就是这样做的,而我也因此得到了现在这份工作。”
陈皱起眉头,“你来这儿的时机比现在好多了。”食物填饱了肚子,酒精让他的脸和四肢都开始发热,他整个人显得精神抖擞,信心也恢复了不少,“但你也别太得意。即使你现在住在粪肥巨头的大楼里,在我看来你仍然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你现在是黄卡人里的老爷,可那又算得了什么?你现在的成就还没到我的脚踝骨那么高,大人物先生。”
马平睁大眼睛,笑了起来,“对,那是当然的。也许有一天我会达到那样的高度。我一直在努力向你学习。”他微微笑着,朝陈衰老的躯体点了点头,“学习一切——除了这段不太完美的结尾。”
“听说顶层有吊扇,是真的吗?上面很凉快吧?”
马平朝着黑乎乎的大楼看了一眼,“是的,当然。也有消耗自己的卡路里,让那些吊扇转起来的人。而且他们还为我们提水,充当升降机里的压舱物,每天上上下许多次。这些人就以这些方式为粪肥巨头效力。”他大笑起来,又为陈倒了些酒,“不过,你说得没错。这算不了什么,一座可怜巴巴的破宫殿罢了。
“但现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和我的家人明天就会搬走。我们已经拿到了居留许可证。明天,等我拿到薪水的时候,我们就会搬出去。我们不再是黄卡人了,不用再给粪肥巨头的手下交保护费,白衬衫也不能再刁难我们。我们已经在环境部办好了手续,上交了黄卡。我们现在是泰王国人了。我们会成为移民,而不再是入侵者。”他拿起酒杯,“这正是我在此庆祝的原因。”
陈皱起眉头,“你一定很高兴。”他喝完杯中的酒,把酒杯砰的一声放在桌上,“但别忘了,出头的钉子一定会遭到重锤敲打。”
马平摇着头,咧嘴笑了笑,眼睛里闪着光,“曼谷不是马六甲。”
“马六甲也不是巴厘岛。我们一直是这么说的,然后他们拿起弯刀和发条手枪,把我们同胞的头颅堆在排水沟里,让我们同胞的血顺河流向新加坡。”
马平耸耸肩,“那是过去的事了。”他朝待在锅边的夜宵摊主挥了挥手,又要了些食物,“我们现在要在这里安下家来。”
“你以为你能做到?你以为那些白衬衫不想剥了你的皮挂在家门口?你不可能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在这里,我们是不会有好运气的。”
“运气?三荣先生,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迷信了?”
马平要的菜上来了,是炸得很脆的小螃蟹,和着盐粒和热油,用筷子夹起就可以放到嘴里直接嚼碎,每一只都只有陈的小指尖那么大。马平夹起一只,放进嘴里嚼碎
“三荣先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软弱了?你解雇我的时候说过,运气都是自己创造的,现在你怎么又说你没有运气?”他朝人行道上吐了口唾沫,“我见过一个发条人,它活下去的意愿都比你强。”
“Fangpi(放屁)。”
“不!是真的!我的老板经常去的酒吧里就有一个日本造发条女孩。”马平倾身向前,“她看起来就和真的女人一样,还会做一些很恶心的事情。”他咧嘴笑着,“能让你下面硬起来。可你不会听到她抱怨运气不好。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白衬衫都想把她扔进化粪池,甚至为此付钱也行。但她还是住在那座高楼里,每晚为所有人跳舞,展示她没有灵魂的躯体。”
“这不可能。”
马平耸耸肩,“随你怎么说,反正我亲眼见过她。她甚至不用忍饥挨饿。她什么都吃,也能挣到钱,就这么活了下来。什么白衬衫啦,宗教狂热者啦,王国的法令啦,甚至还有那些特别憎恨日本人的人都奈何不了她。她在那儿跳舞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她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也许是靠贿赂吧。或许某些丑陋的法郎热衷于她那种污秽的表演。谁知道呢。她做的那些事情是真正的女孩绝对不会做的,能让你的心脏停跳。但当她那么做的时候,你会忘记她是个发条人。”他大笑着瞥了陈一眼,“别和我说什么运气,整个王国的运气全加起来也不够她活这么久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不会是因为她的前世因缘,因为她压根没这种东西。”
陈福生耸耸肩,没有表态,又夹了几只螃蟹放到嘴里嚼。
马平咧嘴笑着,“你知道我说得对。”他喝完杯里的酒,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运气是靠自己创造的!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有个发条人在公共酒吧里表演谋生,而我为一个特别有钱的法郎工作——要是没了我,那家伙屁事都干不成!所以,我说的当然是对的!”他又倒了一些酒,“别再那么顾影自怜,你得专注于如何从不幸的境地里爬出来。洋鬼子就从来不考虑什么运气啊命运的。你看,他们现在不是又回来了吗,像新研发出来的病毒一样!收缩时代也没能阻止他们。他们就像柴郡猫一样侵入了我们的地盘。但他们的运气是靠自己创造的。我甚至不能确定因缘之类的东西对他们到底有没有作用。这么愚蠢的法郎都能成功,我们华人没理由一直这么卑微。自己的运气靠自己创造,你解雇我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你说我的厄运是自己造成的,一切只能怪我自己。”
陈抬起头来看着马平,“也许我可以到你的公司工作。”他咧开嘴笑着,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不是那么绝望,“我可以为你懒惰的老板赚到更多的钱。”
马平合上眼睛,“啊,这不太好说,不好说啊。”
陈明白这其实就是委婉的拒绝,他应该就此闭嘴。但尽管他想要退缩,他的嘴却再次张开,继续恳求道:“也许你需要一个助手?保管账本什么的?我会说洋鬼子的语言,我以前跟他们做生意时自学的。我会很有用的。”
“我自己的工作已经很少了。”
“但如果他真的像你说的那么蠢的话——”
“是的,他确实很蠢。但还没有蠢到发现不了办公室里又多了一个人。我们的办公桌相隔只有这么远。”他用手比画了一下,“你觉得他会注意不到他的计算机踏板旁边有个瘦骨嶙峋的苦力蹲在那里吗?”
“那如果到他的工厂里去工作呢?”
但马平已经开始摇头了,“如果我能帮助你,我会帮你的。但能源链是由巨兽工会垄断的,至于流水线上的检验员,工会有规定,不允许招收外国人。另外,恕我直言,没有人会相信你是个材料工程师。”他摇着头,“不行,确实没办法。”
“随便什么工作都可以。铲粪也行。”
但马平只是更加使劲地摇着头,而陈这时也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舌头,命令它不要再提出更多的恳求。“没关系,没关系。”他硬挤出一个笑容,“我相信我总会找到工作的。我并不担心。”他拿起酒瓶,不顾马平的抗议,把剩下的酒全都倒进了马平的杯子里面。
陈举起半空的杯子,向这个在各方面都已经超过了他的年轻人致意,然后头向后一仰,一口吞下剩下的酒精。桌子下面,几只几乎隐形的柴郡猫在他骨瘦如柴的两腿间走动,等着他离开,就好像他会蠢到留下些食物残渣一样。
清晨到来了。陈福生在街道上游荡,试图找到一份早餐。用钱买的话,他根本付不起。他穿过小巷,市场里弥漫着鱼、香菜和柠檬草的气味。榴梿堆散发出臭味,它们满是刺的表皮上有着锈病感染留下的红色痕迹。他觉得自己也许可以偷到一只。它们原本应当是黄色的表皮上确实有些污垢,但果肉仍然很有营养。不知人体摄入多少锈病病毒才会陷入昏迷。
“想要吗?大甩卖了,五铢买五个。很便宜,不是吗?”
向他吆喝的女人嘴里没有牙齿。她微笑着,露出牙床,重复道:“五铢五个。”她讲的是普通话,显然认出了他的身份。虽然他们继承了同样的文化,但她显然比他幸运,因为她生在泰王国,而他则不幸地投生在马来亚。她是一个受到国王和家族庇护的潮州华人。陈强压下心中的嫉妒之情。
“我看四铢买四还差不多。”他说了个双关语,四和死同音,“这些都得了锈病啦。”
她恼恨地挥了一下手,“五铢买五个。都是很好的。非常好。刚刚摘下来的。”她拿起一柄闪光的弯刀,把一只榴梿从中间切开,露出干净肥厚的黄色果肉。新鲜榴梿的甜腻气味升腾起来,弥漫在他俩周围。“看!里面是好的。摘下来的时间刚好。还是安全的。”
“我可能会买一个。”其实他一个也买不起,但他还是忍不住这样回答道。被当作顾客的感觉确实不错,他意识到这是因为他身上穿着的衣服,那套黄氏兄弟的套装提高了他在这个女人眼里的身价。要不是这套衣服,她是不会和他搭话的。整场谈话全都不会发生。
“多买点啦!买得越多,省得越多。”
他强挤出一个微笑,不知道这场本不应有的讨价还价该如何收场,“我只是一个老人,我不需要太多。”
“你太瘦啦!多吃点,吃得胖一点儿!”
她说了这句话后,两人都大笑起来。他思索着该如何回话才能让这场如同志般的交流持续下去,却一时语塞。她看出了他眼中的无助,摇了摇头,“哎,老人家,现在人人都不容易。你们一下子来得太多了,没人能想到情况会变得那么糟。”
陈羞愧地低下了头,“很抱歉打扰了你,我马上就走。”
“等等。”她把切开的半个榴梿递给他,“拿着。”
“我买不起。”
她不耐烦地比了个手势。“拿着吧,帮同胞一把也是件好事。”她咧嘴一笑,“再说这一个锈病有点严重,好像也不能卖给其他人了。”
“你真仁慈。愿佛陀对你微笑。”正当他接过这份礼物时,他再次注意到了她身后堆成小山般的榴梿。它们全部非常整齐地堆成一堆,上面有着大块的污渍和锈病留下的血红色痕迹,与马六甲街头的华人人头堆是如此相像:他的妻子和女儿们似乎正张着嘴望着他,好像在无声地控诉着。他把榴梿丢在地上,一脚把它踢开,疯狂地在外套上擦着手,似乎这样就能擦去他手上的鲜血。
“哎!你怎么把它丢了!”
陈福生几乎没有听见那个女人的叫喊声。他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眼睛却始终注视着地上那只榴梿斑驳的表皮和流出的果肉。他发疯般地向四周望了一眼。他必须脱离人群,必须躲开这些拥挤的肉体和弥漫在周围的榴梿气味,这种气味卡在他的嗓子眼里,让他窒息。他一只手捂住嘴,开始奔跑,推开其他的顾客,在推推搡搡中艰难前进。
“你去哪里?回来!Huilai(回来)!”但那女人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人群中了。陈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推开那些购物篮中装着莲藕和紫色茄子的妇女,躲开农民和他们的竹制手推车,绕开盛放着鱿鱼和蛇头鱼的水桶。他就像一个行窃被发现的小偷一样在市场的巷子里奔跑着,头脑中除了奔跑什么也不剩,也完全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想躲开他的家人和同胞的头颅堆。
他奔跑着,奔跑着。
最后,他跑到了被称为石龙军路的开阔大道上。被碾成尘埃的粪便和炽热的阳光笼罩了他全身,人力三轮车的车流从他身边驶过,棕榈树和低矮的香蕉树在明亮的天空中闪烁着微弱的绿光。
陈心中的恐惧正如到来时一样突然而迅速地散去了。他停了下来,双手抚膝,一边喘息一边咒骂自己。愚蠢,愚蠢。你不吃东西,你就会死。他站直身子,想转身回市场去,但那堆榴梿又在他的脑海中闪过。他跌跌撞撞地跑出巷口,几乎再一次窒息。他不能回去,他不能面对那些泛着血红色的榴梿堆。他弯下腰,胃里一阵阵地痉挛,但从空空荡荡的胃里呕吐出来的只有黏液。
终于,他用黄氏兄弟缝制的袖子擦了擦嘴,强迫自己站起身来,迎视周围这些外国人的目光。如果这是由一片外国人组成的海洋,那他必须学会在这片海洋中游泳。他意识到在他们眼中他才是外国人。他厌恶这种感觉。再想想马六甲,他们的家族在那里已经生活繁衍了二十代,完全扎下了根,但他在当地人心目中同样是个闯入者。他家族的辉煌历史只是华人扩张的一个脚注,这扩张如今被证实短暂得如同午夜的凉风。他的同胞就好像散落在地图上的米粒,虽然洒下的时候非常随意,但现在已经被非常认真地全部清除掉了。
在深沉的黑夜里,陈福生将尤德克斯旗下的红丝牌马铃薯从车上卸下。这些都是土豆大佬的财产。得到这份工作他感到很幸运。即使此时他的双腿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似乎随时可能彻底罢工;即使此时他的双手接过巨象上卸下的沉重麻袋后开始颤抖,他仍旧感到十分幸运。今天晚上他会得到的不仅仅是工作的报酬,同时也有机会偷取到一定量的货物。因为这一批马铃薯是为了避免新一波结痂霉菌的侵袭——这已经是今年的第四波变种了——而提前收割的,所以它们的个头都很小,但它们仍旧营养丰富。个头小意味着它们更容易被装进苦力的口袋里。
胡老四蹲在比他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把车上的麻袋卸下来递给他。众多拉车的巨象不安地来回挪动着,发出哼哼声。陈需要用手里的钩子接住胡老四递来的麻袋,然后完成卸到地面的最后一步。出钩,钩住,甩动,放下。一遍,一遍,再一遍。
陈并不孤单,这份工作还有很多“帮手”。居住在高楼贫民窟里的女人们在梯子周围忙碌着。每当他把一只麻袋放到地上,她们就会伸出手来,仔细摸索这个袋子。她们用手指感受每一寸粗麻布,试图找到上面的破洞、裂缝,寻找幸运的礼物。她们反复摸索从他手上卸下的货物,几乎每一条线都要摸上一次,只有当苦力们推开她们,扛起麻袋走向土豆大佬的仓库的时候,她们才会略微退开。
刚干了一个小时的活儿,陈的手臂就开始打战了。三个小时以后,他几乎站不住了。每卸下一只麻袋,他都在吱嘎作响的梯子上摇晃着,一边喘息一边摇头甩去眼睛里的汗水,同时等待着下一只麻袋。
胡老四从上面往下看了一眼,“你还好吧?”
陈回头看了一眼。土豆大佬正看着他们,数着他们这批人究竟搬了多少袋马铃薯到他的仓库里。他的眼睛不时扫过陈周围停放的货车。在他身后,五十个不那么幸运的人正隐藏在阴影里,默默地注视着这边,每一个人都远比土豆大佬本人观察得更加仔细。陈站直身子,伸手接过又一袋马铃薯,努力不去想那些注视着这边的眼睛。它们在等待着,如此礼貌,如此安静,如此饥饿。“我很好,很好。”
胡老四耸耸肩,又将一袋马铃薯顺着车沿卸了下来。他的位置比陈要好些,但陈没法因此而怨恨他。他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吃些亏。再说这个工作是胡老四找到的,他有权选择好一点儿的位置。在下一个麻袋到来之前,他还有一点儿休息的时间。毕竟,是胡老四把陈带来做这份工作,否则他今晚上是会挨饿的。这很公平。
陈接过袋子,把它放在下面伸出的一只只手里,然后一扭,脱开钩子,袋子落到地上。他的关节好像散开了一样,软绵绵的没有力气,大腿骨和小腿骨似乎随时可能分家。热量让他晕眩,但他不敢要求其他人放慢速度。
又一袋马铃薯递了下来。女人们的手向上伸着,就像纠结在一起的海草,相互触碰、推挤,充满了渴望。他没办法让她们把手缩回去。如果他对她们叫喊,她们会退开,但马上又会回来。她们就像柴郡猫一样没法控制自己。他将袋子从几英尺高的地方扔到地面,然后又向上伸出手,等待着正从车上卸下的又一袋货物。
接住这一袋货物时,他的梯子突然发出巨大的吱嘎声,往一边倾倒。它沿着大车的边缘滑动了一段距离,然后又突然被什么东西卡住了。陈左右摇晃着身体,靠那袋马铃薯掌握平衡,试图重新找到重心。女人们的手在他身边不断摸索着他手里的袋子,有的推,有的戳。“小心——”
梯子再次侧滑。他像一块石头一样掉了下来。女人们立刻四散分开。他摔在地上,膝盖传来一阵剧痛。装着马铃薯的袋子彻底散开了。在那一瞬间,他担心的却是土豆大佬会说什么。然而就在这时,身边的女人们都开始尖叫起来。他翻了个身,仰面躺着,只见上方那辆大车开始整个儿摇晃起来。人们叫喊着向四周逃开。巨象拉着车突然开始向前用力,因此大车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一条条竹梯像雨滴坠落一般纷纷倒了下来,落在地面,发出类似爆竹的响声。巨象又转了个弯,开始后退。大车从陈的身边滑过,把倒地的竹梯压成了碎片。虽然拉着沉重的货车,但巨象的速度依旧出人意料地快。巨兽张开大嘴,突然发出一声尖嚎,与人类恐慌的尖叫声同样高亢。
人群周围,其他巨象同样开始嘶吼起来。它们的吼声震动了整条街道。巨象用后腿直立起来,力量与速度的爆发彻底拉断了连结大车的束带,把大车像玩具一样甩到一边。人们惊慌地躲避在空中飞舞的束带,一棵樱桃树上的花朵纷纷掉落。疯狂的巨象再次吼叫一声,抬腿踢了大车一脚,大车侧倒着向一边滑过去,擦过陈的身旁,两者只隔着几英寸。
陈福生试图站起来,但他的腿完全不听使唤。大车撞在一堵墙上,竹子和柚木发出难听的吱嘎声,然后爆散开来。巨象对着大车又踢又撞,试图彻底甩开它,重获自由。陈双手撑地,拖着沉重的身体和完全不听使唤的双腿从大车旁边逃开。在他周围,有些人在吼叫着发号施令,试图控制住巨象,但他没有回头去看。他的精力集中于前方的鹅卵石道路,他必须脱离巨象的威胁范围。但他的腿仍旧不听使唤。它似乎背弃了他,憎恨着他。
终于,他爬到了一堵防护墙下面。他奋力站了起来。“我很好,”他告诉自己,“很好。”他小心翼翼地试着动一下腿,往下用了点儿力。感觉不太稳当,但并不怎么痛,至少现在不痛。“Meiwenti(没问题)。Meiwenti。”他低声说道,“没什么问题。只是摔了一下,没问题。”
人们仍在吼叫,而巨象也依旧在尖声嘶吼,但他合肥白癜风医院白殿疯从哪里长
转载请注明:http://www.feilvbina.com/fbzz/7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