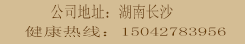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旅游 > 菲律宾华人在中华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以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旅游 > 菲律宾华人在中华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以

![]()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旅游 > 菲律宾华人在中华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以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旅游 > 菲律宾华人在中华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以
陈衍德
〔摘要〕在亚洲最西方化的国家菲律宾,华人在积极融入当地文化的同时,坚守自身的民族文化之根,在现代与传统的互动中,展现了富有特色的菲华文化,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增添了色彩。笔者在数度赴菲调查的过程中,与菲华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生动材料,又在菲律宾华人的主要祖籍地闽南进行了多次采访,亦获益良多。本文通过两方面材料的互补和对照,从办学与教育、经济活动、文化与生活、信仰与风俗等角度,论述了以华人为媒介的中华文化在菲律宾群岛的传播、适应与嬗变,对华人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文化传播中华文化菲律宾华人
华人移民与文化传播的论题并不新颖,但像《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陈达著)和《一个移殖的市镇》(李亦园著)这样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力作并不多见,虽然它们并非以文化传播为唯一的主题。本文力图突破文献资料的限制,并以本人亲自采访所得的口述资料为主要研究材料,论述菲律宾华人在中华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年间,笔者四度赴菲律宾对华人社会进行调查或从事相关的学术活动,大约在相同的时间段,笔者也对闽南侨乡进行了实地调查。在这一系列调查中,笔者积累了不少访谈记录,受访者包括菲律宾各地的华侨华人与闽南侨乡的归侨侨眷。经过分类整理,笔者发现可以利用这些材料从四个方面对菲律宾华人的文化传播角色进行讨论,那就是:办学与教育、经济活动、文化与生活、信仰与风俗。
本文的特点是,对华人移民与文化传播这一论题的讨论,以笔者的亲历场景为感性认识的依托,以采访所得的口述资料为理性探讨的原始材料,并将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本文的探索路径与主要利用文献资料的论文完全不同,乃是一种将不可复制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理性思维相结合的独特的探索路径。
一、办学与教育办学与教育既是菲律宾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基础,又是这种传播的表现。海外华人既在祖籍地兴教办学,又在侨居地(后来成为定居地)兴教办学,两地的这种文化教育活动是互为关联的。华侨子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因而得以提高,从而使他们在中华文化的传播中扮演了更加重要且正面的角色。菲律宾华人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美国殖民当局将美国本土的排华法案援用到菲律宾,限制华工入境,而教师、商人等则不在限制之列。其后果是,“菲华社会发展成了一个只包括商店老板与佣员的单纯的商人社会,这是菲律宾华人与东南亚其他地区华人社会最不相同的地方”。〔1〕另一方面,华文教师也得以顺利地进入菲岛。商人与店员需要比一般劳工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促使华侨子弟努力读书,这使得菲律宾华人重教兴学的传统多增加了一股动力。
菲律宾华人85%来自闽南,闽南侨乡子弟的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在接受笔者采访的菲华人士中,大部分人在出国前都曾在家乡读过书。年出生的厦门禾山人陈永庆说:“我在家乡时已有读书,读私塾也读小学,私塾在高林社,小学在泥金社。我也曾在何厝社读过书。”〔2〕有一部分人还读到中学。出生于年的安溪人陈水池说:“我年毕业于集美学校中学部,年来菲。”〔3〕菲华企业家陈本显回忆其父的经历时说:“我的父亲陈清楠于年在家乡(晋江金井)的毓英中学毕业后,考入了集美学校……”〔4〕甚至在旧时代很少有女孩子读书的情况下,来自闽南侨乡的女性移民在家乡读书的经历也不乏其例。厦门禾山人陈琼英说:“我在家乡就读于寨上湖山小学……读书用的是闽南语,但有学国语拼音。我离开家乡时起码已读到小学四年级,简单的故事书已能看得懂了。”〔5〕
那些在菲岛出生的华侨子女,家长们也纷纷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将他们送回家乡读书,从而打下中文的基础。后来在菲律宾一直读到大学的施水源(晋江人,生于年)说:“我虽然出生于菲律宾,但小时候多次返乡……有一次我与母亲返乡后,就留在家乡读书。”〔1〕这种送子回乡读书的风气,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笔者在20年前采访了厦门市仙岳村的叶建文,他说其父出生于菲,十一二岁被祖父送回故乡读书,“我12岁那年,即年,祖父带我和二弟叶建智(比我小一岁)自菲返厦,目的也是回国读书。”只是后来大陆解放,他们兄弟俩无法返菲,才一直留在家乡。〔2〕
更多的出生于菲岛的华侨子女,或者幼年就离乡赴菲的华侨子弟,只能在侨居地读书,这就促使菲华社会很早就兴起了办学之风。在菲律宾华侨史上,最著名的也是创办最早的3所华文学校是:马尼拉的中西学校、怡朗的华商学校和宿务的中华学校,它们在笔者的访谈录中都得到了反映。高振英(生于年,龙海人)说,中西学校校长颜文初乃其妻之姑父,其妻赴菲后于年应聘于该校任教;年他本人亦以教师身份赴菲,也在该校当教师。他们夫妻是在家乡的小学读书时成为同学的,后来分别上了中学,之后又都曾回到母校当小学教师。〔3〕叶贞良(厦门人,年生于菲)说:“父亲在怡朗就读于华商中学,中学毕业后又返回中国,就读于暨南大学(当时设在上海)……父亲曾经先后在马尼拉、宿务教过书,结婚后才开始做生意。”〔4〕叶淑英(厦门人,年生于菲)在年接受采访时则说:“我在(宿务)中华学校读书,毕业后留在母校教书……中华学校后改组为东方学院,年我出任副院长,年出任院长至今。〔5〕
20世纪上半叶华人聚居地已遍布菲律宾群岛,只要当地具备办学条件(资金、生源与师资),基本上都兴办了华校。从吕宋岛最北部的亚巴里,到棉兰老岛南部的纳卯;从米沙鄢群岛到苏禄群岛的各主要港埠,都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华校,其中不少还是既有小学又有中学的完全学校,使华侨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上世纪60年代菲律宾实行华校菲化政策,这些学校又都实现了教学语言从中文为主到英文为主的转变,既保持了华校的本质,又适应了时代的变化。战前华侨对其子弟的文化水平要求并不太高,“当时的华侨青年,读书只要读到会记帐、会写信就行了”。〔6〕战后则不同,随着英文能力的提高,不少华裔青年中学毕业后还考入大学,甚至出国留学。而且无论战前还是战后,“一个华侨子弟读的语言起码有四种:国语(中文)、闽南语、英语、土语(他加禄语或其他土著语言)”。〔7〕这样,华裔青年在接受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还具备了与土著人民进行文化双向交流的语言能力。
无论是在菲律宾办学还是在闽南办学,菲律宾华人都不遗余力。在菲律宾办学兹举苏禄和纳卯为例。在苏禄群岛的首府和乐市,有一所创办很早的华校——同仁学校,包括中学和小学。曾担任过该校董事长的黄锦狮(他还曾任苏禄中华商会理事长)说:“(20世纪)60年代该校大约有师生八百多人,其中教师(包括中、英文教师)约四十几人。菲化以前该校以中文教学为主。起初学生都是免费就读的,后来半费,再后来全费。另外,各位董事都要负责向人数不等的贫穷学生提供学费。学校的资金来源多种多样,也有通过选美活动筹措资金的。”〔1〕在棉兰老岛的纳卯市,中华教育会是该市最早建立的华侨社团。曾任该会董事的洪昭美说:“战后教育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华人商家,他们以货物航运费的百分之十这样的比例,捐钱给教育会。此外,以前华人学生上学不收学费,战后两年,学校开始收取学费。”〔2〕各地都有一批热心的华商,他们以社团为依托,兴办华校并维持华校的经费,使华裔青少年无论贫富都能入学。
在闽南办学兹举厦门为例。旅菲富商、厦门禾山人林云梯、林珠光父子兴办前埔云梯学校的事迹,一直为家乡父老所传颂。“林氏父子对家乡的最大贡献是营建并维持云梯学校……云梯学校规模宏大,是西洋式的楼房,学校设备一应俱全,实验室、运动场、草坪花园等都有专人管理。本村的孩子全部就读于此校……当时(战前)全校约有学生四五百人。禾山的许多孩子,甚至有些内地的孩子,都就读于此校。所有入学者一律免费就读。学校原设有中学部和小学部……”〔3〕这是笔者20年前采访前埔村长者林永周时他的一席谈话。林云梯的一个儿子林聚彪也说:“战前我家在厦门的布店(胜隆布店)收入和房租(共有48座楼房)收入都用于云梯学校的经费开支。”〔4〕可惜云梯学校后来毁于日军炮火,笔者已无处寻觅其踪迹。民国时期,厦门禾山的旅菲华侨,只要拥有一定财力,都会出资在家乡办学。笔者采访到的这类事实就有:后坑村叶兆君创办侯卿小学堂、祥店村众侨设立祥店小学、钟宅村众侨设立钟宅小学、仙岳村叶安顿创办仙岳小学、吕厝村吕希福创办禾公小学等等。
在菲律宾兴办华校与华人社团的支持分不开,在闽南办学更与菲华社团关系密切。财力雄厚的华商可以在家乡独资办学,一般的华商则非联合起来不可。“当时(民国时期)闽南较大的乡在马尼剌(拉)都有同乡会,不过大半负责教育经费的筹措而称为校董会,后来才改称同乡会”。可见同乡会的初始功能就是为家乡办学筹措经费。“当时闽南各乡由南洋华人出资设立学校如雨后春笋,学生人数大量增加”。〔5〕倘若闽南人没有离开故乡下南洋谋生图发展,以大量资金支持家乡办学,闽南教育事业绝对不可能有如此的发展局面。从菲律宾流回的资金成就了闽南侨乡教育事业的辉煌,而来自侨乡的人才又源源不断地补充进菲律宾的华商队伍。与此同时,菲律宾华校也为菲华社会培养了无数人才。加上许多华裔青年被送回故乡学习中文,再返菲继续深造,使得适应中菲(西)文化的两栖人才大量增加,从而使菲律宾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和作用更上层楼。
由于菲华社会逐渐由侨居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华人越来越认识到适应当地社会的重要性,加上偏远地区华校的不足,因而有更多的华裔少年儿童进入当地学校(“番仔学校”)读书。华校菲化后以英语教学为主,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当地少年儿童进入华校学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进入以土著民族学生为主的大专院校学习。凡此种种,都使菲华两族的学生有了越来越广泛的接触。菲华两种文化的双向互动也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悄然进行的。
这里也不能忽略这样一种事实,亦即许多没有机会进入正规学校读书的华人青年,也边工作边自学或上夜校学习。“战前我工作十分辛苦,虽然想读书,但没有时间……但我还是千方百计挤时间读书,没有时钟,就用自来水龙头滴水来计算时间……我初来菲一年多之后,就能粗略地读懂当地文字了……我住‘山顶’,周围多‘番仔’,所以学起来快。与我的同辈人相比,我的他加禄语很不错。”〔1〕这是在国内已小学毕业的吕孙博(年生,年赴菲)的口述。“父亲让我晚上补习英语,白天在店里干活。我学英语学得较快,很快地与菲人打交道也用英语了……我晚上到‘丹心’夜校学习英语……我从小学第四册的英语课本读起……我抓紧点滴时间学习英语,工作也很忙。我也很喜欢读书,但家境不允许……我读夜校读到中学毕业(英文)。”〔2〕这是在国内已读到初中一年级的黄庆仁(年生,年赴菲)的口述。华人青年店员在业余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与土著人民所产生的互动,是另一种形式的菲华两种文化的互动。
当一个民族的成员向另一个民族传播本民族文化,同时又接受对方文化时(文化传播必然是双向的),他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就个人而言,文化输出和输入有自觉和非自觉两种情况。知识和能力水平高者,自觉的情况更多,反之亦然,即水平不高者不自觉的情况更多。在自觉的情况下,他能更全面而理性地将本民族文化优秀的一面展示出来,也更能接受对方文化的优秀成份。菲律宾华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知识和能力水平的提高,使他们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并汲取菲律宾土著民族文化的优秀成份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步。
二、经济活动社会经济生活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华人在侨居地的主要活动是经济活动,他们与土著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大多数情况下乃是寓于经济活动之中。随着华人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扩展,其文化传播范围也愈益扩大。而随着华人在各经济领域活动的由浅入深,其对所在国文化的影响也从表层进入实质。这样的一种发展规律,也完全适用于菲律宾华人。
西班牙统治后期,对华侨居住地的限制逐渐放宽,华侨的分布开始扩散,至美国统治时期已遍布整个群岛。中、南吕宋是二战前菲律宾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华侨最密集的地区;北吕宋和米沙鄢群岛中部次之,华侨的密集度亦如是;其余地区的经济较不发达,华侨分布亦较稀疏。华侨通过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大体上与华侨分布的情况相匹配。
那么,以华商为载体的文化传播,是经由哪般路径进行的?年赴菲的郭辅昆(晋江人,年生)说:“加牙鄢省(Cagayan)的亚巴里(Aparri)是个大埠头,它位于吕宋岛的最北端,加牙鄢河的入海口,该河流经四个省。当时马尼拉与北吕宋因受大山阻隔,陆路难行,办货多由水路,在马尼拉用船载货经海上到亚巴里,再溯加牙鄢河而上,沿河各村社都有华侨开的店,船上的货就批发给这些店。由于在贸易上处于重要地位,所以亚巴里聚集了许多华侨。”〔1〕在《菲律宾与华侨事迹大观》一书中,作者对亚巴里的描绘,印证了郭氏的说法:“亚巴里埠……华侨商店,在21年前(约年前后)余初至该埠观光时,则大小约有百家,商业颇形繁盛,因彼时交通未便,嘉牙渊及依沙迷拉两省所辖各社镇,所需货物皆仰给于亚埠。华侨商店……较大资本者,则设有贩船,以运输货物,溯流沿河贩卖兼收买土产。”〔2〕口述与文字的相互印证,让人们看到华侨经济的触角,乃是由“点”到“线”再到“面”地扩展开来,这一路径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路径。
社会经济文化的活力首先有赖于人们的工作精神,而华侨的勤奋工作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年赴菲的吕孙博(晋江人,年生)说:“吕宋岛南部描东牙示省(Batangas)的丹拉湾(Tanauan)……我的二舅在那儿开了一间店,我就在店里当伙计……像我这样的雇员,早晨五点就起床,晚上十点多十一点才得休息,‘墟日’起得更早。每周有两个墟日。当地人有‘赶墟’的习惯,就是住在村庄(当地人叫Barrio)的人们到集镇或乡镇(华侨称之为‘社’)里来,把农产品拿来卖,再买日用品回去。遇到墟日我们就十分紧张,常常要等到下午两三点钟散墟后才能吃午饭。舅舅的店收购农产品,再雇别人的车,将其运到马尼拉,卖给华侨的店,又从马尼拉进货运回去。我们收购的农产品主要有玉米、绿豆等,销售的东西则无所不有。”〔3〕这种遍布城乡的华侨“菜仔店”,通过其老板与雇员的勤奋工作,使由它们构成的购销网络成为整个国家经济肌体的神经末梢,从而调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活力。
在中国,上述那种“墟市”至迟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并且日益发展成固定的集市,进而形成繁荣的市镇。菲律宾20世纪上半叶商品经济的发展,依稀可见中国历史的影子。倘若此说不谬,华商即为二者之媒介。前引陈笑予书中,更有一段文字与吕氏的口述相印证:“亚南棉洛示社。本社原无侨店之创设,平时侨商与土人贸易,端赖每星期间之‘墟日’(原注:即临时市场,通常三日一市或一星期一市,谓之墟日),多由拉牛坂之侨商将货物运抵该社菜市内排摊与土人买卖。迨至年,蜂牙丝兰省与三描礼示省之长途公路完成后,交通便利,始有粤侨两家前往经营面头炉(面包店)兼菜馆。闽侨三家,其中木业一家,位于菜市对面;两家百货商,位于菜市边。其后又增四家,计共九家。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再有增加,现已有三十家。据该社名商冯秉东谈称:该社战前华侨人数不多,商业未见兴盛,战后侨店突增数家,华侨人数骤多,商场渐见扩大,营业日趋繁荣。”〔1〕
菜仔店(菲律宾人称为sari-saristore)“原为华侨庞大商业中最小的小本生意,它所发售的货品大部是普通家庭日常生活必需品”。乡间的菜仔店往往比城市的菜仔店规模大,因为除了零售之外它们还有收购土产的功能。“华侨在全菲开设的菜仔店数目,据二次大战前的估计,单在马尼拉市及其近郊就有三千多间,全菲合计可能超过八千间”。〔2〕菜仔店还是华侨各种轻工业产品、食品工业产品的推销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来自中国的果蔬、布匹等商品,以及来自香港、新加坡乃至日本的商品,经由华侨进出口商输入菲律宾,也由菜仔店销售。“五十年前此地的蔬菜许多是从闽南进口的,通过厦门转口到马尼拉。比如包菜、芋头、蒜等。这些蔬菜用轮船运来……一些批发商把蔬菜进口到马尼拉后,再卖给零售商。”〔3〕旅菲华侨洪应士于年回国在漳州创办四维农场,“四维农场开办经营期间,马尼拉有一家公司代理该农场产品的进口和销售,是由洪应士的一位兄弟负责经营的。公司将从中国进口的水果和干货批发给零售商人”。〔4〕曾在棉兰佬的目加兰开设菜仔店的钟武变说:“我的店里什么都卖,有中国货也有外国货,比如布匹就有中国产的也有日本产的。”〔5〕从父辈起就在苏禄经营菜仔店的陈清汉也说:“我家在苏禄的店,货物的来源,有来自马尼拉、香港、新加坡、日本的,我一两个月就要来马尼拉一趟,其他几个地方只要写信去,对方就把货物运到苏禄。”〔6〕那些来自中国的商品,可以说是最直截了当的中华物质文化的传播。
而菜仔店在文化传播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物质的范畴。菜仔店“直接与消费者发生关系,每一间菜仔店都有一大群菲人消费者,他们的交易由一仙(分)至数元不等……也有不少消费者每天到这些菜仔店赊取物品,等到星期六发薪时才还钱”。〔7〕菜仔店是华菲两族人民经济关系、信用关系乃至情感关系的建构者和维系者,那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以润物浸无声的方式沟通着双方的心灵。有学者感叹道:“华侨菜仔店商人……一年三百六十余日,天天都是开门十六小时以上,随时为菲大众解决食与用的问题;随时给周围邻里的菲人民赊欠,甚至还给予借贷;而售货则以最低廉价格,有时不但不加上利润,反以赔本的价钱出售。”〔1〕这是一种最具实质意义的文化传播,它在使华菲两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密不可分的同时,使双方的情感互为交融,从而抵消了因种种原因出现在二者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下面两段访谈录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祖父的碾米厂乃是收购稻谷加工出售。菲律宾的稻子一年三熟,每逢收获季节,山顶(乡村地区)的菲人就把稻谷运进城里来,卖给碾米厂,再买城里的东西回乡下去。碾米厂则将加工后得到的大米卖给城里的居民。我们住的巴隆庞是座小城市,城里大多数是华侨(印象如此),菲人大多数住在郊区和乡村。做生意的大多数是华侨,当地人既不太懂得如何用钱,也就不懂得做生意,而且他们的土地多得很,要种地也就无暇做生意。”〔2〕这是受访者叶建文、叶建智兄弟在回忆其祖父经营菜仔店兼米绞(碾米厂)时的一段谈话。在菲律宾的小城市或乡镇,菜仔店和各种农产品加工厂往往是合二为一的。另一位受访者黄建宗在描述其父在菲经商的情况时则说:“有些华侨在大城市里做生意做不好甚至失败,日子不好过,就转移到‘山顶’即乡村去。乡村里有农场主,他们的农场生产稻米,农场里还有碾米作坊。华侨商人收购大米往往预付订金,农场主在稻谷收获后把它加工成大米,然后交付华侨商人,华商再将大米运到城里卖给米店,有的米店即华商本人自己开的。”〔3〕乡村的菜仔店兼具收购农产品的功能,店主往往预付部分款项给农产品生产者,这样有利于后者度过出售农产品之前的青黄不接时期。
二战后菲律宾政府的零售业菲化政策,迫使许多华侨放弃菜仔店的经营。除了继续由菲籍华人经营一部分菜仔店外,更多的菜仔店转归菲人经营。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因为原先不善于经商的菲人,从华侨菜仔店的经验中获益匪浅,他们逐渐成为零售业的主体,实在得益于华侨的商业文化。而许多华商以此为契机,转而投资实业,兴办工厂,进而产销兼营,创办专业商店,从而使自身的经济活动提高了一个档次,其商业文化也进入到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而这种商业文化又对菲律宾商界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
“华人办的小型工厂多是家庭式的,工人大多在五十人以下……从马尼拉派往南岛的推销员,仅针织品这一行就有两三千人,竞争十分激烈……我当推销员时,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往南岛跑一趟。以后有了自己的工厂,我也自己往南岛推销自己的产品……我们都尽量和华人的店发生关系……华人经商成功的秘密还在于,把积累下来的资金尽量投入经营,而不是生活享受……我们店在南岛的销售网点主要分布在宿务、怡朗、描戈律、仙道斯将军(市)、纳卯、古达描岛、三宝颜等地,大约在每一个城市都有三四家最主要的客户。”〔1〕这是年开始在马尼拉办厂的陈炳安的自述。
如果说零售业菲化政策反面推动了华人办厂的话,那么菲律宾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浪潮则是从正面推动了华人办厂。一开始华商办厂多是小规模的,既便如此,集产销于一身的华商也十分重视销售网络的构建,这种网络是以华商之间的信用为基础而构成的,所以小小的资本也能发展起来。加上华商抑制自身的消费,将资金大量投入生产和经营,所以华人工业开始在菲律宾工业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华人企业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这一时期正好又是华人由侨居转变为定居的时期,华人工商业逐渐成为菲律宾民族工商业的组成部分,所以这种企业文化对菲律宾土著民族工商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文化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父亲手中接掌在宿务的一家布店的叶长江回忆说,他在外地学校读书时几乎没有菲人朋友,“回到宿务后,我才结交了一些菲人朋友,尤其在接管布店生意后,与菲人交往更多。当时客户的90%都为居住在其它岛上的菲律宾人,来往要靠船只。当时,他们的信用比现在好,我家与菲人客户的关系也很融洽,这些菲人朋友会在某些节日邀请我们参加活动,我们也会乐意撑船前往。”〔2〕战后从马尼拉迁至纳卯的吕孙博也说:“来到纳卯之后,我自己做了生意。我与当地菲人的接触更多的是由于生意上的往来,但与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3〕正是这种从生意上的朋友到生活中的朋友的发展历程,使菲人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华人文化的影响。
在菲律宾,华人的社会角色既是经济角色,又是文化角色,而且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经济角色是文化角色的物质基础,文化角色满足经济角色的精神需求。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化角色沟通了菲华两族的精神世界,从而使两个民族的共同的物质生活乃至社会生活都处于更加和谐的状态之中。
三、文化与生活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语言。侨居民族在向土著民族传播自身的文化时,除了要掌握对方的语言,也要不断巩固自身的语言。如果侨居民族的子弟逐渐丧失了掌握本民族语言的能力,那么他们不仅不能向土著民族传播自身的文化,反而有可能被对方同化。所以本文的这一部分,文化的含义首先指的是民族语言。
菲律宾华人对其子弟的华文能力的培养历来十分重视。除了本文第一部分已论及的通过办学和教育来保证华人子弟的民族语言能力之外,菲律宾华人还注重在日常生活中鼓励青少年讲华语(包括国语和方言)。
出生于菲的陈琼英在回忆她的几个人生阶段时说:“(小时候)在家里我们还是讲闽南话,在外面与同学和当地的孩子就讲番仔话了。在南岛(她家当时住在武运),华侨讲闽南话的人不如马尼拉多,讲得也不如马尼拉的华侨好。我结婚生孩子后,我的丈夫对子女们也是要求他们学汉文,要求他们每星期都要写毛笔字。我的亲家(女儿的公公)也同样是这样。”〔1〕著名华人企业家吕希宗在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时也说:“我虽然生于斯长于斯,但受到的是中华文化的熏陶。祖父对我们兄弟的要求很严格,要求我们在家中都要讲中国话,所以我中国话讲得比番仔话更好。祖父和父亲知道我奠定了读、写中文的基础,才让我去读英文学校。”〔2〕
菲律宾华人对自身民族语言是如此的执着,以至于他们的非华人配偶(俗称“番婆”)不少也学会了讲华语,这样他们的混血的下一代也就具有了华语的会话能力。笔者20年前的一个采访对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祖籍厦门禾山钟宅的钟武变,年生于菲律宾,乃是他的父亲娶番婆所生,7岁随父返乡,13岁再回到菲律宾。钟武变28岁时也娶了番婆。他在第一次受访时说:“我娶的番婆因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并且常与我周围的堂亲、乡亲接触,所以也学会了讲闽南话。她甚至还会打麻将。我还活着的5个子女也都会讲闽南话,可是他们只会用英文读写,而不会用中文读写。我的5个子女也都曾经回到中国来过。”〔3〕第二次受访时他又说:“我在菲娶的番婆会讲闽南话,她还要求子女们在家也讲闽南话。有一次她对孩子们说:‘你们要是不会讲闽南话,你们的父亲就要赶你们出门!’她不仅会讲当地话、闽南话,还会讲英语。我和番婆一共生了10个孩子,有5个至今还活着。”〔4〕这位可敬的老人多次返乡,给笔者的印象至深。如果他还活着,今天已经是超过百岁的老人了。
当然,语言的使用包括听说读写几个方面。虽然华裔青少年的华文读写能力已经今不如昔,但是年长的华人仍然还是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例如,颇有儒商风范的许龙宣说:“我读的书虽然不多,但经商之余喜欢写些文字……有的还写成文章,在华文报纸上发表。”〔5〕一位喜欢读书的华妇则说:“我有点文化,喜欢读书看报……战争(二战)爆发后,有许多华侨跑到我们那儿(加帛士)去避难,其中有两位先生有点学问,会读文言文,我就跟他们学,学读《古文观止》。到马尼拉后,有一次一位隔壁的大嫂发现我会读文言文,还十分惊喜呢!”〔6〕菲华对自身民族语言的执着加上新移民的补充,菲华社会的华文读写能力尚不致衰退。这就有利于华人通过文字来传播民族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通过自身的民族语言,华人向周围的菲律宾人日积月累地传播着中华文化。与此同时,许多华人通过学习也逐渐掌握了当地语言,这就为土著民族接受中华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文化的含义其次指的是民族心理与文化价值。海外华人特别是年青一代受居住国社会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也是适者生存的必然后果。但是另一方面,其民族心理与文化价值,通过长辈的言传身教,经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海外华人仍然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了民族传统。
一位信仰基督教,但家庭生活仍中西并存的华妇说:“我们家中年青一代有的虽然已不会讲闽南话,但是一些想法仍然是中国式的。”〔1〕这在亚洲最西方化的国家菲律宾,是十分常见的。为什么华裔青年在民族语言能力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却还能继承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呢?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是这样回答的:“即使这些人历来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可是他们通过与其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语言交流,他们吸收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2〕这对于他们固守民族文化之根是十分重要的。
一位有着四分之一西班牙血统的华人青年说:“我的祖父很早就来菲律宾了,他到了美骨区(BicolRegion)南部,在那儿娶了番婆,她名叫EmiliaPavon,这就是我的祖母,祖母是西班牙后裔。”后来他的祖父带着全家回到故乡厦门,祖父于年病逝于故乡,祖母也未再返菲,父亲和叔父则于战后返菲,赚钱寄回故乡赡养家人。直到祖母于年去世后,一家人才又离乡经香港在菲团聚。他说:“祖父保留传统习惯的做法一直在我家延续下来。祖父在世时治家完全是中国式的,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教育子女,与故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3〕连他的“番仔”祖母也深受祖父的影响,要求晚辈们做到父慈子孝、夫妇和睦。可见华人的民族文化之根是很有穿透力的。
海外华人的民族心理与文化价值深植于他们的乡土感情之中。菲华学者施振民曾充满感情地说:“华人社会的第一代移民在原籍故乡生长,亲身尝试过中国农村穷困的生活,因而对故乡贫瘠的土地,古老简陋的住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童年的记忆加上异国乡愁,使上一代华人对故乡产生一份特别亲切的感情,也促成其与中国坚牢不破的认同。”〔4〕这样一种感情也传给了下一代,从而成为海外华人世世代代扮演中华文化传播者的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因此,讨论华人的民族心理与文化价值,就不能不涉及其乡土感情。
下面是三例祖籍厦门禾山,又都出生于宿务的华人之口述节录。叶贞良(年生)说,他一两岁时即随家人返乡,“我有时候住祥店外祖母家,有时候住岭下祖母家,来来往往,就这样一直在家乡住到七八岁,才又跟祖父祖母一起返回菲律宾。我至今对家乡仍有一些印象,所以事隔四十多年之后,当我于年再次返回故乡,还能依稀回忆起孩提时代的往事。我的祖母姓何,是厦门禾山何厝人。我小时候常跟祖母在一起,经常听她讲有关故乡的人和事。我知道的有关这方面的东西,很多都是从她那儿听来的”。〔1〕叶民族(年生)说:“我七岁那年,父母亲带我们全家回到故乡仙岳,我在那儿住了一年多,还在那儿读书。当时唐山的一些风俗习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还记得很清楚。”〔2〕陈耀珍(年生)说,他十一岁返乡读了五年书再来菲,“年父亲在吕厝盖了一座大厝,有两层楼,大厝门外有两尊石狮。年我在离开故乡四十二年之后回到吕厝,我家大厝还在,可是门口的石狮不见了。我一直想把这对石狮找回来,若能如愿,我要不惜一切地把它们运到宿务来,摆放在我家住宅的门口。我们陈氏原来有族谱,后来也散失了,我也想找回族谱,以便让孩子们的名字按辈份的字来排列”。〔3〕
如果不是亲耳听他们说出自己的出生地,笔者是不会相信他们乃是出生于菲律宾的第二代华人移民。他们的举止言谈乃至乡音、外貌,可说与第一代移民毫无二致。其乡土情结既源于其长辈,又源于其幼年返乡的经历,对故乡的眷念一直伴随其一生,堪称民族文化之根代代相传的典型。因此,终其一生,他们也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中华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令人感叹不已。
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价值,都是与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的。虽然华裔青年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但也只是表面的物质形式的改变。年出生于菲律宾的晋江人施水源在谈到包括其子女在内的一家人的生活方式时说:“我的母亲仍健在,与我生活在一起。母亲经常对我的儿子、女儿讲一些有关家乡风俗习惯的事……我感到我的家庭生活仍然遵循着中国的生活方式,但与家乡的生活方式不完全一样。我们在家里吃东西用刀叉,而在以前是用筷子,大约在十年前发生了这种变化,但孩子们仍懂得用筷子。”〔4〕这里还看不出深层次的精神文化发生了变化。是否可以这样说,海外华人所扮演的中华文化传播者角色,在可预见的将来尚不至于发生大的变化。
四、信仰与风俗历史上闽南乡民移居菲律宾群岛,既经历了由此国居民到彼国侨民的变化,也经历了由农民到市民的变化。就农民到市民的变化而言,乃是一种较为长期的渐变。因此,乡土意识一直在许多菲律宾华侨身上得到体现。菲华历史上的闽南地方神崇拜,似乎可以说就是这种乡土意识的表现。可是到了当代,这种崇拜仍然盛行,仅用乡土意识来加以解释就太表现化了。显然这里有一种文化积淀在起作用,这一作用使传统和现代相互糅合,使乡土神崇拜获得了现代的意义,从而承载了华人的民族文化,并使这一文化得以流播。
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中国文化语境中,特别是在下层民众的“小传统”中,对神明的种类并无严格的区分,因此闽南乡民常将所有的神明统称为“菩萨”或“佛”。这种称呼也在菲华社会中广泛流行。一位年迈的归侨这样说:“虽然拜菩萨的习惯随华侨传入了菲岛,但一般是携带家眷去菲者,亦即全家人均在菲者,才在家中供奉菩萨,单身汉拜菩萨的情况则少见。我所在的地方,并未在华侨的商店里看到菩萨。”〔1〕此翁所言乃是20世纪20年代菲律宾南部一个华侨人数很少的偏僻小镇之情形,然亦可见华侨故乡的神明流布之广,虽小镇亦不能免。远离华侨聚居中心的偏远之地或许仅止于家中供奉乡土神,然而像马尼拉这样的大城市,据笔者20世纪90年代的观察,华人商店供奉传统神明的现象倒是随处可见。
由于拥有众多的华人信众,大大小小的华人寺庙遍布整个菲律宾群岛,它们包括佛寺、道观和民间神庙,但后二者有时是难于区分的。无论如何,它们都代表了来自中国的宗教文化。那么,菲律宾土著人民是否受到这种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呢?笔者曾访问过两位曾经长期居住于苏禄、后来移居马尼拉的华人长者,他们都谈到了苏禄的本头公崇拜。其中一位说:“苏禄与中国的关系历史很长。每年本头公的诞辰之日,苏禄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敲锣打鼓,张灯结彩。本头公的坟墓每到那时就香火鼎盛,许多人,包括华侨和当地人,都到那儿顶礼膜拜。当地人也很信本头公的灵威。此外城里还有本头公庙……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就有人到本头公庙里烧香。”〔2〕另一位则说:“苏禄本头公的香火很盛,不仅华人信,当地人也信。本头公的墓在城外,城里另建有本头公宫,那是由一位姓张的富商献出一块地皮兴建的,共有两层楼,楼下出租,楼上为宫,宫中有本头公塑像。该宫设有董事会,我也曾担任过董事。”〔3〕本头公是华人所崇拜的土地公(福德正神)的俗称,后来华人又将郑和下西洋的神迹与本头公崇拜杂揉在一起,本头公庙于是广泛分布于南洋群岛。由以上谈话内容可知,苏禄本地人显然也受本头公崇拜的感染,进而也视其为具有灵威的神明。
宗教文化的传播还带动了文化艺术的传播。闽南的提线木偶戏就是这样传入菲律宾的。泉州文化名人吕文俊这样告诉笔者:“正因为泉州木偶戏参与法事活动,所以它逐渐传入南洋。因为南洋华侨中此类活动是十分频繁的……马尼拉有一座包公庙,相传早年有一块黑色的大木头被海浪括到岸边,推也推不走,于是人们认为它‘有神’,便将其置于屋中,随后有人便来烧香,且有灵验,于是吸引了更多的人。人们为它修庙、做生日,包公庙就这样出现了。菲律宾华侨曾来泉州请道士去包公庙,参加那儿举行的盛大仪式。诸如此类的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都少不了木偶戏的演出。这样,木偶戏便在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的滋养下更加流行。”〔4〕
宗教文化的传播甚至推动了医药文化的传播。中医药虽早已随华人移民传入菲律宾,但接受中医药的人群一开始仅限于华人患者。而华人寺庙为扩大影响,为信徒义诊施药逐渐成为其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一些菲人也到那里求医求药,这就在无形中推动了中华医药文化的传播。马尼拉保安宫即为一例。保安宫奉祀闽南神医大道公(保生大帝),常年开展义诊和施药活动。在宫中举行的“扶乩”活动中,正、副乩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为问事者开药方;在该宫供信众抽取的签当中,则有支药签;该宫还备有各种中草药,供信众免费索取。保安宫文书兼总干事苏子蔚对笔者说:“有(一位)菲律宾小姐Anabell,同时患有心脏病、眼疾和足疾,行动不便,须以拐杖助行。经人介绍来本宫求治,据乩示‘解替’(除却病魔)并派中药治疗,月余乃痊愈。遂将其拐杖送宫中留念。”〔1〕
在菲律宾,宗教融合是东西方文化交相互动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华人宗教融入了菲律宾的(或西方的)宗教成份,菲律宾本地的宗教也融入了一些华人宗教的因素。将这种现象视为双向的文化传播,亦未尝不可。在吕宋岛南部的描东牙示(Batangas),据说年有人从海中捞起了一尊神像,被称为Caysasay,于是当地人为它盖了一座神庙加以供奉。后来华侨来到了这里,将其视为妈祖庙,那尊神像也被当作妈祖加以祭拜。〔2〕华人与菲人的信仰熔于一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昭示着菲华两族的文化在互动中逐渐产生重叠,而华人信仰的内在精神也经由菲律宾神明的外在形体得到展示。
在马尼拉有一座颇具名声的大千寺,笔者曾数度访问过该寺。主持人苏超夷向笔者这样介绍说:“本寺主殿神坛上供奉着三排神(像),共六十五尊,来自四十六国。当中一排的正中央,是广泽尊王,其右是圣王娘、关圣夫子、包王公……其左是玉皇三太子、孚佑帝君、水提尊王……此外还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各主要宗教所崇拜的诸神。(本寺主神)宇宙神亿光然则不在三排神当中,而是位于三排神正前方、整个圆形主殿正中心的位置……本寺受到菲律宾社会各界的景仰。华人的宗教要打入菲人社会谈何容易,可是本寺做到了。我曾应邀到圣托马斯大学主讲神学,还被授予奖牌。”〔3〕笔者还亲眼看到,在一次大千寺的“圣寿大典”仪式上,许多菲律宾的达官贵人都送来花篮,包括当时的副总统埃斯特拉达。这一事例展示了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宗教信仰传播方式:将源于中国本土的神明(广泽尊王,福建南安地方神)与虚构的神明(宇宙神亿光然)同室并尊,再将古今中外的神明(包括西方宗教诸神)囊括无遗,共祭一堂,从而向异族信众畅开了祭拜的大门,进而使中华宗教文化传播于无形之中。
菲律宾华人的宗教生活,与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一样,具有世俗化的特点,它迎合了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民间的好尚,从而模糊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界线,甚至使两者合二为一。这种情况为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国民间的“小传统”文化,在适应菲律宾当地环境的前提下广泛地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华人的神明崇拜与祖先崇拜往往相互交织并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前文提到的那位信仰基督教,但家庭生活仍中西并存的华妇说:“洪家(她的夫家)虽信佛教,但不十分热心,然而在祖先崇拜方面仍做得很周到。每逢十一月一日‘亡人节’,家人都要举行祭祖仪式,摆上供桌,向祖先敬奉饭菜,但仪式的举行不是在家里,而是在华侨义山,在家中已不再设神主牌位,只摆照片,在生辰和忌日时摆上鲜花。在义山的祭祀仪式中则要供‘三牲’。我的父母亲信基督教,所以也没有在家中祭祖的习惯……继母信佛教,所以我们按照她的习惯,在她去世后按佛教的方式来纪念她,如到佛寺里‘做功德’、烧纸钱等。”〔1〕所谓“义山”,就是华人陵园。华人到那里去祭拜祖先,大多已由清明节改为亡人节。从这位华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华文化在传播中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入风随俗地融入了当地的天主教文化,但传统因素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这种传统还因来自故乡的影响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强化,从而使那些已经菲化了的华人,或者那些仅有部分华人血统但文化上已非为华人的人们,出现了文化回归的现象。年笔者陪同加拿大学者魏安国(EdgarWickberg)教授访问泉州地区时,曾任中共泉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郑炳山(当时已退休)告诉我们说:“菲律宾政府的粮食署署长,父母亲是石狮祥芝人,虽然他本人已经菲化,但仍于年5月回乡看望父母亲的出生地。菲律宾政府的财政部长曾来信给泉州市侨办,要求查找他的祖籍地,我们为他找出是晋江清濛。他也是完全菲化、西化的人,但他说他仍准备回来祭祖。”〔2〕由此可见,祖先崇拜这一中华文化传统,在那些已非为华人社会成员的人们的身上得到了复兴。此亦可视为文化传播之现象。
以风俗习惯为形式的文化传播远不止这些。在同一次访问中,笔者还听到了时任晋江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姚嘉潭的一番谈话:“华人出洋后还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传统,没有忘记家乡,一些人还要寄钱回乡养家活口。‘在家处处好,出门条条难’,所以怀念家乡,还保留了家乡的风俗习惯。尽管学了当地语言,但保留了家乡的语言闽南话。风俗习惯的保留较典型的是农历的使用,春节回国与家人团聚,清明节回乡扫墓,都与农历的使用有关,也就是说保留了重要的传统节日。婚丧喜庆的习惯也保留了下来。与此同时,华人在海外也吸收了西方文化,又把这种西方文化带回家乡。侨乡的建筑样式有许多就是中西合璧的。”〔3〕
姚氏谈话中所说的华人庆祝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使笔者想起年春节在马尼拉唐人街看到的情景。下面是笔者的一段日记摘抄:“(春节那天)下午我又到了王彬街……整条王彬街被人群、汽车、马车塞得满满的,两旁各式各样的商店也是顾客盈门,还不时听到鞭炮声。尽管数月来绑架案层出不穷,弄得华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此时此地倒是一番乐而忘忧的节庆景象……据说马尼拉唐人街的春节气氛并未比往年减色……这里的华人已入风随俗,以圣诞节为最重大的节日了。农历除夕之夜只不过各家相聚吃一餐较好的饭而已。不过春节也有其有别于其它节日的特点。一是各商家竞相在店门口烧纸钱;二是许多人家买了成串的小桔子挂在门前,以示吉利;三是人人争着买甜糕、吃甜糕。这些活动在圣诞节和元旦是见不到的。”〔1〕菲律宾华人欢度春节的习俗,已经感染了土著人民,使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华人的这一节庆文化。笔者亲眼所见,唐人街所在区域,菲人也与华人一样充满喜庆气氛。
姚氏谈话中所说的华人仍讲闽南话一事,本文第三部分已经论及。这里从文化习俗传播的角度再稍加谈论。由于华人使用的许多器物仍以闽南话称之,久而久之菲人也接受了这些称呼。另一方面,闽南语也接受了许多菲语词汇,甚至一些抽象性词汇。在泉州颇具名声的民间文化研究者庄为玠说:“闽南与菲律宾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木屐、豆干、豆腐由闽南传入菲岛,而番薯等从菲岛传入闽南。语言方面,菲律宾他加禄语接受了闽南话的大量词汇,如‘目阶’即木屐的闽南话音译。而许多菲语、英语的词汇也传入闽南。如菲语‘吗地’(死的意思)就在闽南广泛流传。英语outside原意是球出界,引伸为事情搞糟了,作为后一个意思的outside也在闽南普遍流行,这也是从菲岛传入闽南的。”〔2〕
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华社会对源于故国故土的文化习俗之传播,又从口头形态上升至文字形态。前文提及的许龙宣,在与笔者交谈时说自己在经商之余喜欢写些文字。他编写的小册子:《分类注释闽南谚语选》〔3〕和《晋江地方掌故》〔4〕,就是体现了菲律宾华人用文字来传播故乡文化的良苦用心。谚语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含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当它们形成文字后,更易于保存流播。这一道理亦可用来说明掌故由口口相传到文字记载转变之意义。此外,菲律宾华人社团也以自身力量来从事文字传播乡土文化的工作。其中一例为,菲律宾安海公会在侨乡相关人士的配合下,出资印行了《晋江民谣百首》〔5〕一书,仅从上述三本书来看,源远流长的闽南信仰风俗将会在异国他乡重放光彩,应该不是没有依据的异想天开。
信仰与风俗层次上的双向交流,是文化传播的高级形式。这一层次既包含了价值观、人生观的成份,也包含了生活方式的成份。而无论何者,都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当菲华两族在这一层次上充分地相互沟通理解后,就可大大缓解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的矛盾,从而达致和谐共处的理想目标。
***
所谓文化传播(culturaldiffusion),是指文化特质或丛体由一个社会或群体散布到另一个社会或群体的过程。〔1〕本文从办学与教育、经济活动、文化与生活、信仰与风俗等四个方面,探讨了菲律宾华人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现实中,这四个社会生活领域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文化传播中华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多面相的,而且它们是相互交融的。随着华人知识和能力水平的的提高,他们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他们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其色彩变得更加鲜明,其作用变得更具影响力。其结果是,中华文化优秀成份的流播愈益凸显,而对土著文化优秀成份的吸纳也更为顺畅。本文并不注重从理论上探讨海外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内在机理,而是注重从点点滴滴的生活实际出发深入地论述其发展进程,以便弥补此前学界多从宏观而非微观上对此进行阐述的缺陷。
一位到菲律宾作田野调查的西方人类学家在解释“什么是菲律宾人”这个问题时,引用了受访者的话说,“他是一个说英语的马来人,有一个西班牙的名字,吃的则是中国食品”。受访者还接着说:“菲律宾人是一个混合物,早在西班牙人和美国人来到此地以前,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因素就已经成为菲律宾文化的一部分。”〔2〕这位受访的菲律宾人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菲律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无论从历史上来看抑或从现实中来看,都是如此。其中,中华文化早已构成菲律宾文化的一个有机成份。既然这样,还有必要继续
转载请注明:http://www.feilvbina.com/fbly/73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