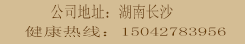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故事 > 菲律宾又点兵,东南亚天生爱搞事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故事 > 菲律宾又点兵,东南亚天生爱搞事

![]()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故事 > 菲律宾又点兵,东南亚天生爱搞事
当前位置: 菲律宾 > 菲律宾故事 > 菲律宾又点兵,东南亚天生爱搞事
地·图·会·说·话
中国人会把彻底忘记一件事情形容为“丢到爪哇国去了”,通过这种形容,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在古典时期的中国人心目中,爪哇岛算得上是一个极远之地了。虽然按照绝大多数古代中国人的理解,爪哇岛应该是一个化外蛮荒之地,但在南洋群岛中,它是能够承载人口最多的岛屿。
南洋群岛即马来群岛,也是欧洲人口中的“东印度群岛”。这片岛屿与中国隔海相望,自古就与华夏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由于热带气候的影响,华夏文明在南洋群岛遇到了同样来自热带地区的印度文明,以及精于海上商贸的阿拉伯文明的挑战。
撰文
温骏轩
▼▼▼
南洋群岛之殇
占据南洋群岛的国家目前共有6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新加坡,以及那个年才独立的东帝汶。把南洋群岛的每一个岛屿都研究透彻是不可能的,连当地人也未必了解这两万多个岛屿的情况(绝大多数为无人岛)。
因此,我们仅需把注意力放在其中几个人口集中的大岛上。这些岛屿分别是吕宋岛、棉兰老岛、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苏拉威西岛、新几内亚岛。其中,吕宋岛、棉兰老岛归属于菲律宾;加里曼丹岛由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瓜分;苏门答腊岛、爪哇岛、苏拉威西岛,以及新几内亚岛的西半部则是印尼的领土。
需要说明的是,东南角的新几内亚岛目前虽然被印尼占据了一半,但在地理上被划在了大洋洲。从地缘及种族的角度来看,这一划分也不无道理。“马来群岛”的称谓来源于这些岛屿上的主体民族——马来人,而处在这一岛屿东南方向的一些小岛,包括新几内亚岛,其上的族群却与马来人并不相同,这里的原住民是更为原始的美拉尼西亚人,他们的人种及语言一直是人类学家们感兴趣的话题。
新几内亚岛没有得到充分开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无论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还是之后,新几内亚岛都不处在东西方的海上航线上。这种边缘化的地缘位置无疑降低了外界对新几内亚岛的影响。这种情况并非绝无仅有,从澳大利亚到夏威夷的南太平洋地区其实都存在这种情况。由于很少受现代文明的干扰,这些岛屿至今仍保留着很多原始人类文化的遗存。
另一个这样的特例是马来半岛,由于地缘文化和地理位置的原因,这个中南半岛的狭长突出部更适合作为南洋群岛的一员。出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我们这里所指的马来半岛,仅指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所占据的那一区域。
研究海岛与研究大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大陆地区,由于国家密集,我们往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山脉河流上面,这些自然分界线往往会成为族群的战略平衡线,并最终成为国境线。而岛屿本身就是一个单独的地理单元,地理位置一目了然。它们的重要性往往体现在身处海洋中的位置,能否处在重要航线上,将极大影响它们的地缘价值。此外,各岛屿的农业、人口潜力不同,也会影响它们彼此之间的地缘关系。
关于马来人的来源现在还没有定论,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更愿意相信马来人是从中国南部(百越族)南迁中南半岛,再通过马来半岛进入苏门答腊岛,之后再向东扩散直至菲律宾群岛的;另一种说法是马来人是沿着那条走出非洲的南线(印度—中南半岛),然后通过马来半岛进入南洋群岛的。
基于地理结构的原因,人类迁移的路线与文明交流、商贸往来的线路,大多数情况下是重合的。不管马来人最初是从哪个方向迁入南洋群岛的,马六甲两侧的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都应该是南洋群岛中人口最先迁入的区域,并且最早有机会与外来文明频繁交流。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克拉地峡与马六甲海峡在东西方贸易中先后起到的重要作用得到验证。
结合地缘位置和岛屿的体量来看,在我们罗列出来的南洋群岛主要的岛屿中,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应该最有机会成为南洋群岛的地缘核心。然而实际情况是体量远小于苏门答腊岛,并且看上去也不在航线之侧的爪哇岛,长期成为南洋群岛的地缘中心。直至今日,爪哇岛西部的雅加达依旧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
印尼虽然号称“万岛之国”,但主要的部分也就是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爪哇、苏拉威西四个总称为“大巽他群岛”的岛屿群。而其中面积最小的爪哇岛(还不到苏门答腊岛的1/3,跟安徽省差不多),现在的人口却有一亿之巨,差不多相当于印尼人口的一半。在古典时期,人口数量可以说是衡量地缘实力最重要的参数。因此在爪哇岛上建立的王国,也很自然地给它在与周边岛屿的竞争中加分。
爪哇岛这巨大的人口承载量,源于它出色的农业条件。像爪哇岛这样的热带农业区,与东亚大陆那种以大面积冲积平原为基础的农业,在地理环境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在东亚大陆所处的温带地区,土地平整、水资源丰富的低地区通常是能够承载多人口的区域。
对于温带平原上的居民来说,只要摸索出河流的运行规律,并进行相应的水利建设,就能够得到成片稳产的农田。而那些上游高地来水,在为平原地区提供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还为下游地区的农作物生产提供了富含营养成分的土壤。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温带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低地区的现状。
不过,这些温带区的农业经验到了热带区,特别是赤道附近的热带核心区,就完全不适用了。在南洋群岛所处的区间里,终年高温多雨,使得这一地区的水土流失情况非常严重。一方面,在高温的情况下,土壤中农作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会更加容易溶解;另一方面,年复一年持续数月的雨季,很容易将溶解在水中的营养成分冲走,在容易积涝的低地区,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与世界上大多数的高地区相比,南洋群岛的很多岛屿(尤其是爪哇岛)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活火山众多。虽然其中有些不安分的活火山,隔上个若干年就可能喷发一次(一般最少也要间隔上百年),逼迫生活在其周边的居民逃离家园。但只要火山喷发结束之后,人类又总是回到火山地区,继续他们的“危险”生活。这是因为火山地区的火山灰土是极肥的土质,并且土壤的透气能力、保水能力也强,非常适合农作物的生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爪哇岛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爪哇岛有座火山,几乎全岛都被火山灰覆盖。在火山灰周期性的补给下,岛上的居民无须像东亚民族那样精耕细作,以及不间断地改良土壤,就能够获得丰富的物产,容纳更多的人口。
正是由于南洋群岛的核心农业区都在那些被火山灰覆盖的高地之上,因此即使在农业技术发达的今天,印尼在试图扩大本国的耕地面积时,也主要把方向锁定在与爪哇岛地理条件类似的苏拉威西岛,而对拥有南洋群岛最大平原的加里曼丹岛缺乏兴趣。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爪哇岛都不在主航道上,但它本身的农业条件十分优越,使得建立于此的王国本身就成为有吸引力的市场,而不仅仅是以一个补给点、中转站的身份出现在东西方交流的通道上。
此外,爪哇岛与马六甲海峡、马来半岛之间的地理距离并不远,因此那些为南洋群岛带来文明的外来者自然不会忽视爪哇岛的存在。相比之下,位于南海东部的吕宋岛、棉兰老岛的位置就过于边缘了,这使得它们在西班牙人从另一边开辟新的东西方交流通道时,才终于出现在了地缘政治的舞台上。
事实上,在马六甲海峡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主航道之前,爪哇岛的地缘吸引力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东晋时期的名僧法显在远赴印度拜求佛法之后,就随着海上商船绕道爪哇岛,以考察南洋群岛上的宗教形态。
要是当年吴承恩写《西游记》时,把主角唐僧换成早两百多年西游求法的法显,那么现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僧人就应该是法显了。只不过取经路上所受的磨难,应该会有一半发生在归来的海路上—“海怪”肯定会多上不少。
虽然马来人在南洋群岛上占据了几个主要的大岛,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大岛上,但就这些岛屿所具有的纵深来说,并不足以产生高一级的文明。换句话说,它们只能从欧亚大陆吸收文明因子来发展自己的文化。不过好在这些岛屿正好处在东西方交流的海上通道上,因此马来人总有机会通过商贸活动,从外部吸收文明。
离南洋群岛距离最近的文明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文明,以及以印度为主的南亚文明。尽管在古典时期,这两个文明与南洋群岛的海上距离显得很长,不过由于地处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上,这两个文明还是对这些岛屿上的马来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单从地理距离来看,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南洋群岛距离东亚、南亚这两个文明地区的距离都差不多。从这个角度看,两大文明渗透入马来文化核心区的机会也
应该差不多才对。但事实上,印度对南洋群岛的实质影响要大大强过中国。比如那个以苏门答腊岛为基地向爪哇岛扩张的三佛齐,所选择的国教是佛教;而长期处在南洋群岛地缘中心位置的爪哇岛,岛上诸王国则选择了婆罗门教作为国教;甚至在中南半岛上,印度的文化影响也要强过中国(中国仅在越南北部的影响要更强)。
从地缘的角度出发,便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这场文化争夺战中会长期处于下风了:纬度及气候这两个基础地缘因素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前我们在东亚部分曾经分析过,古中国的核心区基本处在暖温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两个区域尽管在细节上有诸多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气候特征就是四季分明。这使得在中国核心区的绝大部分地方,古天文学家所制定的“二十四节气”都能够起到指导农业的作用。
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均属于热带地区。如果再细分,可以划分出热带季风性气候、热带雨林性气候,以及热带海岛性气候。不管怎么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热带地区不再四季分明了,它们基本上只分为雨季和旱季(或称干季和湿季)。不过,那些海岛上一年四季都是雨季,而南亚次大陆的旱季则要长得多,以至于还可以再分为“冷季”和“热季”。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对古代中国农业与气候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关于黄河流域在前古典时期的气候问题,目前正在研究当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那里的气候属于亚热带气候,和现在长江以南的气候类似。
当然,那个时候黄土高坡及华北平原还是森林茂盛的区域,气候特点与现在已被过度开发的长江中下游相比还是有所区别的,物种也更为丰富。比如处在黄土高坡与华北平原过渡区的河南,古称“豫”,有一种解释说“豫”就是“持矛猎象”的意思。这多少能够说明在华夏文明开始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特点是什么样的。
因此,东亚农业就起源于这种不同于热带地区的、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下,只是黄河流域现在已经变成了温带气候。这便是最初产生于黄河流域的节气亦能适用于长江流域的原因。
之所以要讨论华夏文明所适应的气候,是因为华夏文明的本质是最为彻底的农业文明,它在古典时期的传播范围是受限于当地的农业条件的。华夏文明中的农业特点过于突出,以至于由此而产生的文明因素中,气候和环境的特征也过于明显。比如,我们的传统节日基本都与节气有关,春夏秋冬的变换是文人墨客重点描述的对象。
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古中国人将这些文化概念带给热带地区的那些原住民时,他们会多么茫然。而对于同属于热带地区的印度文明来说,这些障碍就少得多了。最起码,从南亚次大陆迁移过来的人可以在岛上基本保持他们的生活习惯。最终,印度文明所产生的文化覆盖了南洋群岛以及中南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中国的北回归线以南地区究竟如何划分“热带”与“亚热带”,并没有一条很清晰的分割线,但最起码在云贵高原以及珠江流域的边缘地区,已经明显属于热带气候了。华夏文明经过两千年的努力,应该说已经初步适应了热带地区。华夏民族在热带边缘地区的生存经验,在古典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对华夏文明的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气候的原因决定了在古典时期,即使有来自东亚大陆的移民进入南洋群岛,也不可能从事他们所适应的农业生活,亦不能与当地人分享他们所熟知的文化常识,最终只能融入当地文化。这一点在中南半岛上也有所表现,所不同的是由于地缘上关系更为紧密,可以依靠不间断地沟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华夏文化的影响力。
从郑和七下西洋开始,中国才真正地将南洋群岛纳入视野。尽管中国随后又恢复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民间的海上交流一直没有停下来。明朝在立国之初“突然”将视野扩大至南海及印度洋,这与元朝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对于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史无前例的扩张行为,不同的民族从不同的角度,会有千差万别的评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扩张行为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东西方的商路都变得更加畅通。当然,习惯于保守农耕文化的华夏民族只是在被动地接受这种开放性。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郑和的远洋探索行动虽然让中国的海商开阔了视野,并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色目人(主要为阿拉伯人、波斯人)对于东西方航线的垄断,但中国人浓厚的农耕情结所引发的恋家心理,使得这些华夏民族的海洋探索者们大多数都没有选择在南洋的海岛上定居,最多只是将华夏的血脉留在了当地。南洋中的一些族群至今仍称他们是中国水手的后代。
华人迁徙图
至于印度文明对南洋文明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宗教来显现的。在克拉地峡部分我们也讲过,在大马来半岛中部最先建立王国的,是来自印度的移民。法显及后来的记录也告诉我们,在伊斯兰教开始成为南洋群岛主流意识形态之前,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和佛教是马来人的主要信仰,至于那些马来国王到底选择哪个作为国教就不一定了。
由于爪哇岛的人口优势突出,使得其承担了南洋诸岛原住民文明圈中心的重任。如果其他农业基础不如它的岛屿希望与之竞争地区中心的位置,就必须有额外的地缘牌可打。这张地缘牌就是地缘位置。
受益于东西方海上贸易量的飞跃,马六甲海峡成为东西方海上的大通道。在这种情况下,位于海峡两侧的地理单元很自然地成为直接的受益者。从技术上看,商船在穿行马六甲海峡之时,可以选择在南面的苏门答腊岛上进行补给,也可以选择靠在北面的马来半岛南部。最先被选中的地理单元,无疑能够率先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并据此来挑战爪哇岛地缘中心的位置。
在这场海峡控制权的竞争当中,最先胜出的是苏门答腊岛。因为无论是与旧原住民文明中心的距离,还是本身的体量,苏门答腊岛的条件都要优于马来半岛南部。直接受益于航线的开辟,苏门答腊岛的东端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三佛齐。从这个中文名称我们也能够感知到,这个能够控制马六甲海峡的马来人国家,是一个佛教国家。之所以选择佛教作为国教,是因为同时期的爪哇岛政权主要信仰的是婆罗门教。这种选择主要是出于地缘竞争的目的。
在随后的历史中,随着东西方贸易量越来越大,实力的天平也开始越发向苏门答腊岛倾斜。终于,在东亚大陆王朝更迭至宋朝的时候,三佛齐王国的地缘实力实现了质的突破,并有机会将势力范围扩张到爪哇岛上(公元10世纪末)。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靠远在东亚的北宋王朝的间接助力。由于宋王朝无力保障陆地丝绸之路的安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量便开始扩大,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三佛齐的地缘实力。
最终在公元年,也就是北宋真宗年间,信奉佛教的三佛齐灭了与之竞争的强敌——爪哇岛上的东爪哇国。纯粹从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这应该算是印度文明在南洋群岛的一场内部博弈。然而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印度文明也没能在南洋群岛笑到最后,因为很快就出现了一个主动扩张能力更强的文明,仅仅用了一百多年时间就完成了在南洋群岛的布局,它就是伊斯兰文明。
阿拉伯人从海上丝绸之路所获得的巨大利益,直接引发了两个地缘后果。一是为了稳定商道,获取更大的利益,阿拉伯人开始有意识地向南洋群岛输出意识形态。只要接受阿拉伯人的文化,便能从海上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并在内部竞争中占据优势。这样的诱惑使得南洋群岛国家发生了连锁反应,也让伊斯兰教在短时间内(前后差不多一百年)在南洋群岛全面铺开。其中,马六甲苏丹国由于其标杆作用和优越的地缘位置,成了南洋群岛新的地缘文化中心。
然而,另一个地缘后果却葬送了阿拉伯人的暴利时代,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格局:由于不堪忍受阿拉伯商人的盘剥(包括同样唯利是图、负责“二次剥皮”的意大利商人),西欧国家开始努力尝试寻找新的航线,以直接和东方进行贸易,欧洲的大航海时代随之开启。
欧洲人开启新航线,也同样来到了南洋诸岛,并且导致伊斯兰世界迅速衰弱。与其他外来文明一样,欧洲人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文明烙印。只不过这次,他们最先开拓的是一块“处女地”—菲律宾群岛。虽然阿拉伯商人们在不遗余力地传播教义时,也曾将菲律宾群岛这片文化低地纳入了目标范围,但因其地理位置并不能像马六甲海峡那样让他们获取足够的利润,所以阿拉伯商人并未太上心,只是帮助当地统治者建立了伊斯兰王国(如苏禄国)。
在西班牙人到来时,当地的原住民还没有完成伊斯兰化进程,因此西班牙人在让当地居民接受天主教教义时,所遇到的困难比其他地区要小得多。另一方面,为了开发这片“新大陆”,西班牙人在传统的南海西侧航线之外,又开辟了一条经由菲律宾群岛、台湾岛到中国大陆的新航线,使得菲律宾群岛从中获益。于是,基督教文化最终得以在南洋群岛获得一席之地。
在这场历经千年的文化渗透大战中,唯一感到遗憾的应该是华夏文明了。其实对照时间表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文明在南洋群岛强势扩张的时期,正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远洋开拓时期——“郑和下西洋”时期。如果中央之国的政治家们能够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并主动参与这场文化竞争的话,华夏文明当时应该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但过于内敛的文化,以及对海洋文化、化外之地的轻视,使得华夏文明从来没有从战略角度设想过这种地缘扩张。
▼
《谁在世界中心》
作者:温骏轩
[点击图片,了解更多]
8年潜心创作,近60幅原创地图
全景勾勒中国大国战略路线图
一本书洞悉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战略博弈格局
中国国家地理图书“地图会说话”系列第一弹!
—THEEND—
转载请注明:http://www.feilvbina.com/fbgs/5132.html